平阳新闻网
木 木
李世斌 编辑 王秀华
1975年,我没有“上山下乡”,而是有幸当了兵。去了部队才知道,我当的是“工兵”,也就是基建工程兵,平时不扛枪,而是扛榔头。部队驻扎在雪域高原上,年复一年地修建一条“天路”。我戏称自己是穿军装的“上山知青”。当个修路兵虽然很艰苦,但我有居民户口“这碗酒”垫底,再苦再累眼前还是亮堂的,因为服完役回乡是能得到安置的。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,有一份固定工作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只铁饭碗端着,心里踏实,眼神就不会迷茫。
与我同时入伍又同时分配到一个班的有两人,一个叫骆林,另一个叫刘小桂。这两人与我是一个地区但不是一个县的,在班里我们仨算是同乡战友。骆林个头小,班长就叫他睡我上铺。
骆林生长在大山里,照他自己的话说是个“山底人”,在家因条件限制没正经念过几年书。分配到班里没多久,骆林就主动讨好我,要我帮他写家书。我说写信又不是做文章,想说啥就写啥,错几个字也没啥。骆林憨憨笑道:“李波,咱俩是睡上下铺的老乡么,你就帮帮忙吧!我说你写,来得快。我手里握支笔比攥把榔头还重哩!”
骆林给我递烟,还帮我点上,我就不好再推辞了。骆林口述我记录,写了满满一张纸。信写完了,我也正好抽完了骆林递给我的第三支香烟。我把信纸递给骆林,说:“你在信上签一下自己的名字吧,这也表示你对父母的尊重。”
骆林从我手里接过圆珠笔,还没写字竟然先将笔头放嘴边哈了几下。我笑道:“哈啥哩,笔管里汁多着哪!”
骆林憨笑道:“以前在家念了两学期书,大字没识一箩筐,倒学了这么个习惯动作。”
骆林手握细细的圆珠笔,挺认真也挺费力地一笔一划签上了自己的大名。我接过信纸念出了声:“马各木木。”我念完之后禁不住“哈哈”大笑起来,说:“骆林啊,真有你的,两个字被你写成了四个字,得拿浆糊给粘一块呢!”
“骆林”被写成了“马各木木”,从此以后我就用“木木”当了骆林的绰号,给叫上口了。
骆林对我叫他“木木”一点也不介意,反而还挺开心的。骆林平时话不多,但只要我俩在一起时相互间的话就滔滔不绝。有不少人不喜欢和他说话,因为他说话与常人不一样——有人说他说话单根筋不会拐弯,有点缺心眼儿,也有人说他的话像根木头棍,不知道何时会冷不丁的被敲一“闷棍”。比如同乡战友刘小桂,一次在工地上发牢骚说在高原上太艰苦了,早知道这样就不来当兵了。骆林却当着大家的面说:“阿桂,咱俩一个村的谁不知道谁呀,就你家那条件,平时番薯丝能吃个半饱就不错了,现在在部队里又没让你饿着,每星期还能吃上一顿大肉。”
刘小桂被呛得满脸通红。我捅捅骆林说:“别当着大家的面直通通地说老乡,给人留点面子么!”
骆林说:“我就这么认为的么,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其实他当兵还是走了点关系的,现在干嘛拿腔调装后悔呀!”
我的父亲是个被暂时“靠边站”的老干部,但还属于“人民内部”矛盾,因此家里生活条件没受到太大影响,隔三差五的吃顿鱼或大肉是寻常事。连里每周改善生活吃大肉时,我就把肥肉夹给骆林,骆林则把瘦肉夹给我。这样的事做多了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,就跟骆林说,以后不这样了,对你不公平。
没想到骆林却说:“李波,你说反了,是我想吃肥肉那,我该感激你才是。我是山底人,以前在家肚子里都是些番薯丝咸菜叶,哪还有油泡泡呢,我做梦都想吃大肥肉哪!”
我这才“恍然大悟”,心想你个木木说话还真够实在的。
骆林这张嘴连副指导员都领教过。一次,全班战士正在工地上迎着鹅毛大雪紧张施工时,副指导员过来了。他扯开嗓子给大家鼓劲道:“同志们辛苦了,茫茫雪域高原上虽然缺氧又寒冷,但大家战天斗地,不怕苦,不怕累,心里头暖烘烘的……”
骆林扶着铁锄把,大声说:“副指导员,我们不怕苦,不怕累不假,但我们是活人,心头还是能感觉出太寒冷啦,哪来暖烘烘的感觉呀……”
副指导员乜了骆林一眼,说:“寒冷是暂时的,革命军人绝不能计较这些……”
万想不到骆林却接着傻乎乎地说:“副指导员,副连长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干活,就你来得少,来了又只会讲大道理……”
我叫了声“木木”,用眼神制止他别再胡说下去。我又瞅了一眼副指导员,看见他脸色微红。副指导员不说话了,从身旁战士手中夺过榔头,朝手心唾了一口唾沫,便挥起榔头朝铁钎“嗨哟,嗨哟”地砸将起来。
我瞟一眼弯腰干活的骆林,轻声骂了一句:“你小子这张破嘴还真神啦!”
我爱好画画,四年的雪域高原生活给了我一生的作画源泉,我的许多获奖作品都是以雪域高原为素材的。当兵的第二年,我为骆林画了一张素描。画面上的骆林站在工地上,肩扛榔头,头戴“雷锋帽”,脸上绽开了单纯而又向往的笑容。骆林对这张画喜欢的不得了,连连赞叹道:“城里人就是厉害,画得这么好,我一辈子都不会丢掉。”
这张素描被下连队的团宣传股长看到了,不久后就传出了我要被调到团宣传股的消息。这个传闻被副指导员给“证实”了。那天在工地上吃午饭时,副指导员端着饭碗蹲到我身边说:“你小子还是个画家呀,以后在团部别忘了多写写画画咱连哈!”
我抑制着内心的兴奋装出随意的口气问道:“真有这事啊,传传的吧?”
副指导员拍了一下我后脑勺说:“团里来电话了,调令已经在路上啦!”
这天是星期六,恰巧兵种报的副刊上又登出了我的这张画,我的那个兴奋劲,可别提有多高了。当天晚上,我偷偷和外班的几个同县的战友撬开大肉罐头,喝了酒。我酒量差劲,喝了二两多烧酒便晕晕乎乎的了。当晚轮到我站岗时,换岗的刘小桂却叫不醒我。无奈,刘小桂只好替我多站了一班岗。这事“可大可小”,往大了说算我脱岗,往小了说好在刘小桂替我补站了,也没造成啥后果。毕竟我们是一支雪域高原上的“工兵”,军事要求不能跟“正规军”相提并论。
如果这事过了也就过了,无非一阵轻风吹过而已。可是在星期天晚上的班务会上骆林的嘴却没放过我。这事是刘小桂私下跟骆林说的,还说接他岗的也知道这事了,只怕纸包不住火了。班务会上,班长提出把我上报连部,作为连长晚点名讲评时的口头表杨人选,理由有二:一是我的画上报纸了,二是明知要调走了还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(看来班长已得知我要调走了)。当班长叫大家都表个态时,骆林却突然提出了不同意见,说了我昨晚因为喝了酒叫不醒脱岗了,不能说是站好最后一班岗。这下子班务会像是炸开了锅了。大家倒没拿我脱岗说事,而是觉得骆林平时与我关系这么好,又是老乡,关键时候怎么会戳一刀子呢?而且还是正面戳过来,真个是“老乡遇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啊!
班长叫我自己说说有没有这回事。我挠挠头皮红着脸许久没有作答,心想这下完了,调团部的事算是泡汤了。
骆林又突然紧追道:“好汉做事好汉当么,李波,你干嘛不愿承认呢?”
骆林这句话算是“补了一棒”了,我无路可退,红着脸说有这事。
第二天晚点名时,连长只是口头批评了我。我挺意外,后来才知道连长手里已经捏着我去团宣传股的一纸调令了。连长和指导员商议后,算是给了我一个“宽大处理”。
我整理好行装去宣传股报到前,骆林和刘小桂来送我。我心里有气,对他俩爱理不理的。还是骆林先开了口,说:“李波,别怪我,我肚子里不藏事,说话也就是巷弄里抬棺材,转不过弯来。那件事我知道没啥大不了的,但隐瞒不说还要受表扬说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就全假了。山底的老人经常说,说假话,会上瘾,毁一生。我唱句山歌给你听,开心笑一笑就不生气了。”骆林说着便扯开他那“含沙量”很高的嗓音唱了起来:“一不是一唉,二不是二,雀儿飞唉飞不快,叽叽喳,叽叽喳,一是一唉,二是二,鹰儿飞得唉高又快,忽拉拉,忽拉拉……”
听骆林唱歌,我忍不住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唉!和骆林上下铺快两年了,我多少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个“怪人”了。我摇摇头说:“木木啊,你确实够木的。”
骆林和刘小桂当完三年兵就退伍回家了。他俩退伍前专门到团部找我道别。当时我的心情不太好,主要是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。我苦笑着跟骆林说:“木木,我多少是受你影响,说话不会拐弯,更不愿意说假话,故有今日。”
骆林说:“是因为你胆小,怕说假话上瘾,干嘛怪我?”
我补了一句:“怕毁一生。”
骆林退伍的第二年,我与提干擦肩而过,终于也是退伍回乡了。我是居民户口,回乡后被安置在县文化馆工作,这对我而言算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,成就了我一生的画家之旅。
那时候没手机,连电话都没普及,交通又不便,我与骆林虽在一个地区,但却一直没有联系过。迈入花甲之年时,我偶遇战友刘小桂,方知骆林退伍后一直在山底老家“修理地球”,其间当过几年村委会会计。我和陈小桂约定“八一”建军节那天去山底会一会骆林。会骆林之前,我凭借当年给他画过的那张扛榔头的黑白素描的记忆,创作了一幅与那张素描一样的油画,只是多了连绵的雪山和飘洒的雪花等背景元素。
“八一”那天,我在山底见到了骆林。骆林事先已从陈小桂那儿得知我们何时来,故早早地就到村口迎候了。我陡一见到骆林颇感意外,他从前稍黑但却光泽的小圆脸如今布满了皱褶,头发也如秋天的树叶,掉得差不多了。我瞪大了双眼惊叹道:“木木,你还是原来的那个木木吗?头发呢?原来的那张小圆脸呢?都哪去啦?”
骆林摆动了几下粗砺的手掌,朗声笑道:“李波,撒泡尿照照自己吧,我看你那头发根就知道,你的一头黑发全假的,城里人就愿意造假。”
我一时语塞。骆林看上去完全是一个种田老头的模样,但他的爽朗和自信又让我深感意外。陈小桂插话道:“李波,木木是狗改不了吃屎啊,都大半辈子了说话还这样,硬棒儿戳屎。”
骆林朝陈小桂瞪了一眼道:“阿桂,我就是一辈子说人话不说假话,哪像你老讲X话,还造假。”
陈小桂不服气,嘴一歪,说:“我怎么啦?我搞的农产品又没给你吃,上个月我还送了几箱没打农药的水果给你,你良心给狗吃啦?”
我拍拍陈小桂的肩膀说:“你俩都说些啥呢,老战友一见面就怼,有意思吗?”
骆林和陈小桂都“嘿嘿”笑了起来。
进了骆林的农舍,我拿出了专为骆林创作的油画。骆林瞟了一眼油画说:“这幅有颜色的画还是你自己留着吧,我不要。”
我不解地问道:“为什么呀?这画的可是你……”
骆林指指挂在墙上的那张素描说:“那上面画的才是我。我说话算数的,几十年来一直挂着没丟失。”
我又问道:“木木,难道是你觉得油画里的你不像你?”
骆林用粗砺的手掌抹一下脸说:“这幅有颜色的我没笑,不像,不像,墙上这张黑白单色的我开心笑着,我还记得当时那么冷的天,心里就想着今天的活快干完了,晚饭连里改善生活,有大肉吃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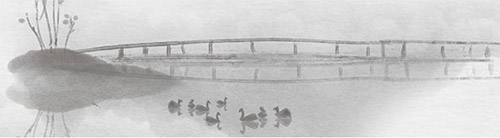
版权声明:
凡注明来源为“新平阳报”、“平阳新闻网”的所有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、美术设计和程序等作品,版权均属平阳新闻网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所有。未经本网书面授权,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、转载或建立镜像。否则以侵权论,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





